http://blog.sina.com.cn/u/490ecb6501000ezb
这是一篇要谈论韩国导演奉俊昊的小文章,在谈论他的时候,我发现我不得不说很多看起来和这个人没有直接关系的话,否则我就无法提出奉俊昊这位导演出现的意义,对我而言,他的出现对于韩国电影是很重要的事件,而对于中国电影也同样会成为很重要的标志。
那么,我先说一些背景的话题。
关于电影的热爱,从我接触到的人群而言,其实就是两类,一类最爱的电影大约是死忠《星球大战》、《魔戒》或者《肖申克的救赎》、《完美的世界》这种电影,另一类言必称各类大师或者带有个性的各类作者,这里面从《牺牲》、《八部半》一直到《蓝丝绒》、《巴别塔》。这两类可以说前者是“类型”的消费者,后者是“作者”的消费者。两者通吃的影迷有,但是大多也不觉得二者可以叠合和沟通,只是吃多了荤腥,换点素净的调剂口味而已。中国电影圈以前大约是言必称大师的,所以在北京电影学院有“大师研究”的课程,而现在大概这个课程即使课名还在,但是戈达尔、安东尼奥尼肯定从讲授内容中消隐,这一变迁在于商业电影成为主流。在这个背景下,类型电影热在中国电影研究机构和制作圈里面也越来越成为显学,但是如果你要仔细去分析现今中国电影的制作,却依然发现我们类型生产的成熟度和能力依然低下,而类型生产所可以提供的接触现实、刺激思考的能力更是缺乏。
关于类型生产的价值判断,大概有如此论述,其一,积极站在电影工业立场上进行讴歌的,因为类型生产的模式的建立,几乎是电影工业成熟度的一个标志,它是大片场和明星制所依赖的叙事生产的平台;其二,积极站在电影艺术和文化反思的立场上激烈的抨击类型生产模式,大概指出类型生产的“神话”或者“童话”的实质,强调类型叙事其实根本隔绝了对现实的真正思考,使得电影几乎成为人民的鸦片。但是无论这两个立场你怎么选边站,对于强调电影可以介入社会现实可以激发思考而言,类型生产都是负面意义的。
奉俊昊的电影被我注意到是因为看到他的《杀人的回忆》,我看了第一遍之后觉得很好呀,于是马上重头再看一遍。两边下来,我就决定将这个作品作为我以后教学的一个案例。我又了解到这部作品在当年的韩国成为票房冠军,于是我每次讲这个作品的时候,都要说一句“这样的作品能够成为票房冠军,那么这个国家的观众是值得尊重的观众。”《杀人的回忆》的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这部作品依赖一个类型叙事的壳(变态连环杀人狂)进行了一种严肃的对韩国军政府事情的社会悲剧进行了反思。在此处,类型生产成为了正面意义的资源,当然,我们也会承认这种类型生产可能使得反思变得有所隐讳,但是“类型”所具有的消费心理能量的释放促使了这种反思直接面对大众,或者说它让严肃的社会议题直接变成建构大众心理的资源。
在整个韩国导演群中,奉俊昊可能不是我们最关注和最了解的,比如,更商业的有姜帝圭,而构成韩国电影国际传播可能的作者群中,我们更多知道朴赞郁、李沧东、金基德、洪尚秀等人,但是相对上述导演而言奉俊昊最为重要的特质就是他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背后的秘密就是我们中国电影最为缺乏的东西。奉俊昊的包容性在于哪些呢?
首先,自然是我们极为羡慕的韩国国家电影政策和这个政策培育的土壤,在1990年代以来韩国电影环境已经形成了艺术和商业生产双赢的局面,这个极为包容的电影生态使得人才出现和人才成熟的效率大幅度提高。譬如,生于1969年代的奉俊昊在2000年做了他的处女作《会叫的狗不咬人》(此处我按照国际英文片名翻译,此片还有如下叫法《更高级一点的动物》、《绑架门口狗》、《同床异梦》),到2003年代拍摄第二部作品《杀人的回忆》时就可以获得巨大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其次,奉俊昊的包容性还在于他自身的知识结构提供了一个当代从事大众文化生成者所需要的支撑力。奉俊昊的社会学背景出生,使得他的第一部作品就具有了优秀的社会议题的关切能力,同时,他又具有将社会议题彻底地电影化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可以将“社会问题意识”和“类型写作规则”叠合在对空间呈现的组成、人物关系的建构和故事结构设计的诸多层面。
最后,奉俊昊的包容性还在于他一方面有将类型进行局部突破和改造的知识精英的意识,这种对类型的突破是将社会严肃思考纳入的必然要求,否则就会彻底被“类型”的“神话/童话”性质扼杀,比如,在《杀人的回忆》中的没有抓住凶手的设计,在《怪物》中“怪物”的形象本身并不是“悬念”的重点,这两个重要的突破其实高度凸显出韩国在“现代性”生成中的困境,而韩国的困境在很大意义上是整个东亚的共同困境;另一方面,他又非常娴熟并且坚持对电影叙事语汇建构在基本的类型电影生成模式上,使得他的电影语汇具有真正难得的大众性、国际性,他的语言是通俗而精确的。
现在,奉俊昊已经彻底跨出了韩国本土成为国际性的电影制作人,他的下一步电影计划是在2008年和法国导演列奥·卡拉克斯一起合作导演电影《东京》。在2004年度,他曾经作为韩国导演的代表参与了东亚三导演的拼盘电影的制作,这次他应该代表至少是整个东亚电影参加这个国际性的计划。我希望奉俊昊导演可以面对东亚问题进行持续地思考,而整个东亚电影的升级促发一种将奉俊昊式的电影生产变成具有东亚整体性的文化现象,这样东亚电影对于大众文化生产的全球格局中才在真正意义上提供自己的核心价值标准——我们的大众文化生产是面对自身问题而在利用自己的思想资源的同时,引入各种文化资源的进行思考,这种思考产品是用高度国际化的语言制作,从而可以进行最广泛的国际传播的。
___________
the host的改编权又被美国人买走了。美国人最近疯狂从外头搜刮二手资源。the departed我一直没看,看到的评论基本就是两极。一般观众(包括我偶像以及著名滴崔卫平女士)都认为比无间道难看很多,而大部分所谓中国大陆的“影评人”都不断强调,这是一部多么NB的片子。崔卫平在南周的文章出来后,howie还用“拍案惊奇”来形容他的感受。我没有任何评论,但是我想起在孙瑞穗博客上看到的一个案例,她说她的学生们有一次问她,那些美国人改的亚洲电影,基本都是亚洲原版的比较好看,反而美国人改的比较受好评,为什么?孙回答说,为什么原版会好看,因为我们永远没法“现代”,永远处于“前现代”。就是“前现代”的这一部分尤其动人。嗯,这个问题竹内好ms早就讲过。我的意思是说,当然,电影有很多评价标准,有“技术性”的一部分,但是,我还是想知道,我们这些所谓的“影评人”自认为是站在超然的立场上仅仅从技术来考查电影的么?我很不怀好意地揣测他们的立场和认同。我看到有个对《怪物》持轻蔑态度的影评人讲,这个电影就是反应了韩国人一贯的民族主义立场,反正坏事都是美国人干的。我们先不说这个电影是不是民族主义,当然,民族主义是很容易被利用的东西,民族主义有很多种表达方式,它可以很狭隘可以很极端,但是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民族主义成了一个纯粹的贬义词了?ps:个人而言,我认同Karl在staging the world里面对民族主义的态度。
关于前现代和现代,正好前两天我没事搜秦晖搜出来一个他自己对和乐钢当年的争论的一个总结。他认为应该用美国的现代性治疗中国的前现代性,而乐钢认为应该反过来。左右之别就这么简单地概括出来。顺便提一句,不上网是不会知道原来汪晖真的被如此多人反感,而秦晖俨然是众人膜拜的宗师,laf
星期三, 三月 21, 2007
杜庆春:让奉俊昊成为一种现象,类型生产的正面意义
发帖者
赋格
时间:
9:54 下午
![]()
订阅:
博文评论 (At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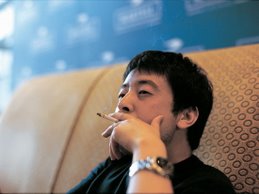







1 条评论:
the host我一直就没看到,很焦急。。
the departed倒是春节时候看了,没有期待的那样精彩,毕竟之前那一大坨影评人的赞誉文章看了太多。是有老马丁一贯的力道在里面,可是电影本身对我没有太大的触及。你说的香港版那种“前现代”的动人之处,觉得很准,就是这样的感觉,而国际上所谓的‘主流’面对这样的动人之处可能是迟钝漠然的。看了电影后,才看到老崔那一篇“伦理想象力”的文,很以为然。斯科塞斯的技术运用或许的确精当得多,那我清楚记得看the departed时,对角色的固着渐渐感到失望。明显的他是略去了无间道努力煽情的一个点。
发表评论